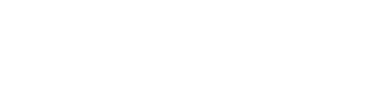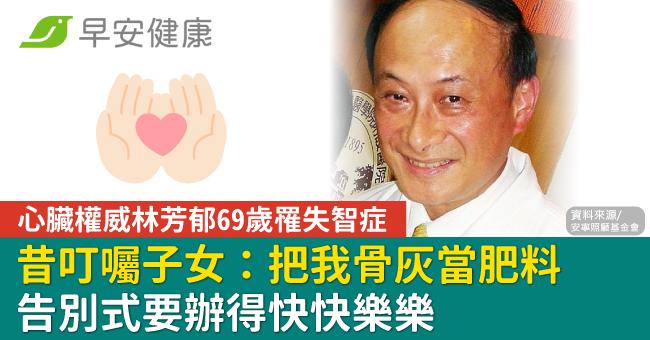
大學畢業之後,我和許多同學立志以醫業救人。所以我選擇當時正在快速發展的心臟外科。這樣的醫師因處理心臟的重症,會碰到很多瀕臨死亡的病人。每一次病人的死亡,都讓我們這些學心臟外科的醫師有罪惡感,因為醫學院的老師,總是告訴我們:「只要有1% 的希望,我們都要全力以赴。」
所以,我們這些聽話的「好」學生總是很努力搜尋研究,想盡辦法發展一些方法去解救病人生命。1995年,柯文哲醫師從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進修回國,開始仿照美國,建立加護病房救命的重武器 ─器官移植、葉克模(ECMO)、人工心臟、洗腎機、人工肝臟、各種人工維生系統……等。有一次,柯醫師很得意地對我說:「在台大的外科加護病房,病人要心臟停止死亡,似乎也不太容易!」但是,在高興這些病人延長了幾個小時或幾天的生命,它的背後有更多的人是付出痛苦的代價。
我第一次接觸到安寧緩和醫療的觀念是在2000年參觀了台大醫院的安寧病房,邱泰源教授介紹給我的。他說:「安寧緩和醫療幫助病人,尤其是癌症末期的病人將痛苦減到最低,盡力把生命和生活品質提高,並且追求善終,另外更幫助家屬度過困境。」。初次聽到,我有一些休克的感覺,和我學醫的基本觀念有很大的落差。
但經邱泰源教授很仔細地解釋,並介紹安寧緩和醫療的觀念是集合醫療和社會、宗教團體一起合作,大家只有共同唯一的目標─ 讓每個人的人生最後一途更加溫馨完美,在他看來,未能協助病人安祥往生,才是醫療真正的失敗。幾年後,我也從黃勝堅教授得知,安寧緩和醫療的觀念他已經延伸至重症病人身上,希望一樣能夠幫忙他們。
「假如有一天要說再見」,我心中已經有譜:人生就像一趟旅遊,有一天目的地到了,我會快樂地下車,不霸佔座位或拉住扶手,還要別人把你踢下車。我曾要求我的小孩:「我的告別式一定要辦得快快樂樂地,參加的人要講一些我的故事或糗事,大家大笑一場。讓每個人都覺得我這一趟旅遊,不虛此行。」告別式後,大家到庭園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樹下,當作肥料。我知道,經過三代以後,沒有一個子孫會認識你的。
至於疾病醫療上,我還是以一個醫師的希望:只要是科學上可以治療的,一定要全力以赴;如果是無太大希望,我會採用安寧療護,無痛安詳地走完全程。
本文獲安寧照顧基金會授權轉載,原文標題/【林芳郁說再見】目的地到的時候,我會快樂下車
看了這篇文章的人,也看了...
繼續閱讀下一篇推薦文章